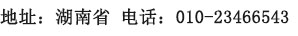1.
很多年前读过一本饮食人类学的经典《甜与权力》。
在书中,人类学家西敏司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而不乏趣味。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 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商品的过程。
过去两三百年的发展,很多事物的变化,确实让人大跌眼镜。现代人时常为了减肥而避之不及的糖,在-的欧洲还是 品,只有贵族才有机会品尝和消费。
2.
中国的情况也类似,《太平广记》中有段记录——汉明帝有位阴贵人,有天晚上做梦,梦到吃到一种特别好吃的瓜。于是汉明帝就开始满天下的寻找, 从敦煌那边找到一种叫做穹隆的蜜瓜,贵人一吃,大呼过瘾……
这位阴贵人,虽然现在已经不红了,但任性的派头比杨姓贵妃足足早了来年。
3.
人类天生就有吃甜食的偏好,主要来自三个方面:
本能反应
甜这种味道是人类在出生之后首先接触到的味道,婴儿在出生之后先吃母乳,而母乳就是甜的。
多巴胺神经元被激活
人在吃甜食的时候,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神经元会被激活,之后它会释放出一种名为阿片类物质的化学物质,当大脑感觉到这种物质带来的兴奋的时候,就会对它产生更多的渴望,所以人在吃了甜食之后还会再想吃。
补充能量
吃糖之后,身体当中的血糖含量就会增高,这样胰岛素就会将其转化为身体的能量。吃的甜食越多,身体当中的能量就越充足,这样人就会产生一种很快乐的感觉。
4.
《糖与权力》的作者西敏司则认为,人类的进食与口味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生理需求,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活动。
食物承载了大量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:人的食物偏好位于其自我界定的核心,表明个人的身份和内涵。在哪里吃,和吃什么,已经不仅仅是食物本身,还有背后的身份和面子问题。
不过现在想想也挺荒谬的:三四百年前,某个英国贵族,神秘兮兮地邀请上几个贵族好友,来到家里,大家一身正装,一众仆人伺候,就是为了能尝口白糖……
如同列维-施特劳斯所指出的:“好的食物”在“吃起来好”之前,首先必须“想到它好”。
5.
中国的吃瓜历史比较久远。
《诗经》中就有“七月食瓜,八月断壶”的描述,当然指的是阴历。(壶是瓠的通假,指的是葫芦)
蜜瓜种植在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,满足了各代中国贵族们的口腹之欲。普通人哪有什么吃瓜的机会?在古代,普通人能不饿死、不战死就已经可以算上盛世了!
所以,西敏司在书中谈到:英国的工人 次喝下一杯带甜味的热茶,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,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型,预示着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重塑。
6.
在古代,即使是贵族和皇室,客观上很多方面也比不上现今的普通人。比如,好的蜜瓜主要产自西北,路途遥远,很难长途运输,所以皇帝吃口好瓜也不容易。
传说,清康熙年间,哈密王为表忠心,将瓜苗直接栽种到木桶之中,运输之时就派自己当地的瓜农随行,一路呵护。等这上贡的队伍到了中原,这瓜也恰好成熟了。
康熙帝算是头一批可以放肆吃蜜瓜的皇帝了,而康熙吃到这瓜之后,确实是被这香甜异常的瓜给征服了。但他并不知道这瓜是什么品种。想着这是哈密国进献的瓜,于是就为其取名为哈密瓜。
“自康熙年间,哈密投诚,此瓜始入中国,谓之哈密瓜。”——《回疆志》
但其实哈密瓜只是哈密地区产的蜜瓜统称,西北还有很多不同 品种的蜜瓜,每个品类的蜜瓜其实各有特点。比如白兰瓜,除了有较高的甜度之外,瓜又香又糯,放在冰箱里冰镇上几芽, 可以替代冰淇淋。
7.
到了现代,生产与运输越来越方便,食物本身得到大范围的供应和传播。
饮食被整个重塑,社会生产的面貌彻底改变,时间、工作和闲暇的性质也与之一道发生了改变。
如何吃的好又吃的健康,成为了更多人关心的话题,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矛盾。
甜的、热量高的食物,仍然可以满足很多人的味蕾和欲望,但如何减肥也成为了全世界的显学。
不过,水果的热量与甜度并不是成正比的,北大医学出版社团队曾经制作过常见水果热量排行表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——热量值 的居然是椰子,而蜜瓜的热量值普遍偏低,尤其是又香又甜的白兰瓜,居然是常见水果中热量值 的水果。
经过多年的试验,致良田今年也开始批量种植银蒂白兰瓜(简称白银蒂),喜欢香糯口感的朋友们,可以大胆下单品尝银蒂白兰瓜吧!不过还需要一点耐心,白银蒂的生长期较长,还需要一周左右成熟。
识别下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