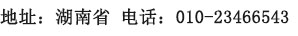一、忆往昔
站在大地圆点瞭望西天,便看到战争、纷扰、史诗,看到很多谁都不曾讲清楚的过往。那方西天,两千年前叫西域,当今叫新疆。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何等值得探究的天方啊,王维却一言以蔽之——喝吧喝吧,到了那边,你只能苦熬着,再也没有人陪你纵情陪你抹泪了——诗人情丝的放纵,使他们太能生杀予夺了!
历史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:自从古人知道东有海洋、中有中原、西有西域开始,中原人和西域人,并没有在纷繁与沉寂、开化与荒蛮、强大与脆微的取舍中甘愿孤立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成为越来越明朗的共存形式,直至归为一统,那一片神秘的土地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汉帝国的西域了。这是中原人和西域人的理智选择,战争从此稀疏。
漫长的两三千年,西域到底经历过了什么,专家们比常人知道得多,但要做到如数家珍,却没有那么简单。考古学家为了证实史书上的只言片语,往往需要花去大量的精力,甚至熬干生命之灯,最终却发现离答案还很遥远。在普通人的概念里,西域就是一方世代沿用的舞台,起起落落,哭哭啼啼,上演过无数幕经世闹剧。但后世的观众看到的,只能是剧中的一些道具残片,诸如西域三十六国、楼兰古城、小河墓地……其实这些哪里称得上直观的残片啊!充其量是一个个擎一副神秘面孔的谜,不单楼兰古国的存亡成谜,小河墓地更是被世界考古人定为最难破解的谜。
二百五十年前,伏尔加河岸一个寒冷的晚上,土尔扈特人首领渥巴锡正在主持秘密会议。也可以说,他正在琢磨、编导一幕有关西域的大戏,场面笼罩着阴森赴死般的悲怆。后来人们才知道,这是一幕叛逃戏,更是一幕*归故里戏,到底该算作什么戏,沙皇俄国人和满清人的定义绝然相反;但不管怎样,这是让我们看得最完整的一出戏了。当初,这些土尔扈特人勇敢地西迁到伏尔加河岸,建立土尔扈特汗国时,这里还不是沙俄的治地。然而,一百五十年后,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沙俄帝国的统治了,决意要作个生死诀别,回到他们的西域去,回到满清去,回到祖国去。
去意已决的土尔扈特人归途经历了可以想到的一切磨难。追杀、瘟疫、严寒没有把他们击垮,虽然伤亡过半,终于还是回到了西域。不难想象,这些平民的出逃,或者叫作回归,很快上升为两个帝国的较量。大清*府没有让土尔扈特人失望,冒着引发战争的危险,把归子们安居在水草丰美的巴音布鲁克诸地。就这样,土尔扈特人将这场戏演成了游子归乡的典范,也演出了西域的自豪感,把世界重重地惊了一跳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说,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它“轰动于世”、“令人激动的了”。
匈奴,一个惊悚的概念,一个雄强的民族对手。讲西域的事,无法迈过它。这样说吧,中原王朝与西域的最早干系,滥觞于它;汉武帝决意收管西域以及那些西域小国甘愿投诚大汉,无不因为它。匈奴之于中原,就像斩不断的蛇头,之于中原与西域,更像横在中间的一道很难逾越的莽昆仑。它可憎,也很勇武,因为它的存在,历史才充斥血性,大戏也才更加精彩。“大汉无中策,匈奴犯渭桥”(李白《塞上曲》),虽然中原最终制服了这个野性十足的民族,但在匈奴人自己看来,彼时的他们风光过、潇洒过。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后,宋将岳飞还发出这样的咆哮: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。”听起来很悲壮,却难以掩饰英雄的无奈。或许,匈奴人还会听出几分村妇气,由此烘托他们的民族自豪感。
大汉王朝不单把匈奴当作劲敌,也当作一种 的试剂。试验场所:西域。试验对象:将臣。试验内容:忠奸。张蹇通过了测试。 次出使西域,虽然被俘,但俘而未降,历经千辛万苦又回到汉朝。西汉大帝没有苛求文臣临敌自裁,只要能回来,就说明心里有着朝廷。况且,这个爱卿张两次出使西域,不仅未辱皇命,还打通了东西经贸往来,也算是大功一件;苏武通过了测试。由使者变为阶下囚,牵累于匈奴内变的偶然事件,但因为无需承担被俘的直接责任,给人家放羊也就放了,朝庭给予了理解。但幸遇宽容,并非好运气,而是因为苏武的信仰和严谨保存了洗清自己的证据,“仗汉节牧羊,卧起操持,节旄尽落”(班固《汉书》),苏武在汉节上浸染十九年羊粪蛋的臭味,西汉大帝却在汉节上嗅出了忠臣的芳香;李广也通过了测试。不顾年迈,自荐出征,可见忠心昭昭然矣。奇功未建,拔刀自裁,又完全符合皇上为武将们设计的路数;唯有李陵,没有逃过这块坚硬的试金石。皇上得出结论,这不是一块真金!弹尽粮绝算什么,你不该活着进了敌人的帐房。活着也就罢了,你不该生生地投降了!汉武大帝在一系列测试中,坚信了本民族的光辉前景,在民族问题上,忠远远胜于奸。于是,他对奸人更加痛恨了,要在爷爷李广和孙子李陵之间制造出强烈对比,对李陵处以灭门九族。他甚至杜绝任何人为奸臣开脱,因此让爱说话的司马迁失去人根,蒙羞千古!
喀纳斯美景胡广平摄二、功勋
按照“是金子就会发光”的模式,可以这样推演一下:“是肥肉总会招来狼的觊觎”。西域算不算一块大肥肉?答案也必须到历史的沉沟里去捡拾。自大汉以降,早已归化中原王朝的西域并非太平无事了,它们所依赖的中原尚且屡分屡合,时强时弱,西域又怎么会静如止水呢?其间经历了多少舔唇之窥、肥瘦之夺,恐怕没有谁去详实统计。到满清中后期,西域已落入多张血盆大嘴,战争在所难免。
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,注定它是自相矛盾的,尤其后期,一方面极力表现出帝国的雄强,另一方面又处处遭揙。于外,被帝国主义的洋枪顶着脑袋,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;于内,反清斗争从来就没有偃息过。当然,把账全记在朝廷头上,的确有失公允,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已成为大势,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在走向衰落,再也无力守住自己碗里的肥肉了。
时至同治三年(一八六四年),西域的戏唱得异常乱,随时有崩台的危险。天山南北的农民反清起义,覆盖大部分地区的封建*权割据,渗透宗教势力的民族仇杀,酷似一堆肿瘤交织在一起,大有耗干这杆肢体之势。然而,最要命的还远不止这些。临近西域有一个浩罕汗国,国中有一个巨恶,叫阿古柏,正是这个主儿趁乱扑向了他垂涎已久的肥肉,迅速将势力扩展到整个南疆和部分北疆,撮合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,后更名洪福汗国,阿古柏自立为汗。本来这种游戏在古代太常见了,一帮人筑起一堵墙,就可以称王立国了,不存在合法不合法的问题。不过,这个阿古柏并不是等闲之辈,毕竟大半个西域已在他的股掌之下了。与此同时,北方沙俄那恬不知耻的馋嘴一直都没有合上,趁乱再次威逼清廷签订了新的条约。又是条约,条约!这些列强也玩不出新的花样,无非是霸占别人的国土家业,还要扯下一块遮羞布挂在脸上。
乱世和英雄互为背景,穿过中间的一面墙,将是翻牌后的异样风光。清王朝该显示其雄强的一面了,大戏的一号主角也该登场了。一代名臣左宗棠尚未弹去平定陕甘回人之乱的风尘,又临危受命,铲灭西域之变。那时他约六十三四岁,临近古稀,大多数人都到了堕志颐养的阶段。然而,英雄从来没有自然年龄,只有名垂青史。
那是一个没有战斗机,也没有战车的时代,甚至偏居内陆的西域也没有战船,茫茫几千公里,全凭布满鲜红血脉的肉体去突奔。但左宗棠铁了心,要把这场戏演成千古绝唱,战前几年就争取朝廷确定塞海并重的防御战略,以获得平定西土的*治基础,同时下手治*队、改*械、备*粮、筹*饷,战时又 制定“先北后南”、“缓行速战”的*事路线。一切充满了智慧的人谋,促使他把战争打得像优美的进行曲。
一些资料是这样记载这支乐曲节律的:一八七六年四月底,开始移师西进。八月十七日占领古牧地。八月十八日收复乌鲁木齐、迪化州城及伪王城。十一月六日再克玛纳斯北城。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四日,左公亲率万人开赴达板,十六日围城,十八日击退增援敌*,十九日克城。二十一日克七克腾木,二十二日克辟展,二十五日克胜金台,遂收复土鲁番,二十六日克托克逊。五月下旬,阿古柏暴毙。之后,清*以破竹之势,开展了东四城之战和西四城之战,战无不胜。至于沙俄,当然也从这种充满快感和惊*纷飞的战火中警而戒,深感伙同其他外贼吞并西域的美梦即将破灭,很不情愿地交还了伊犁。随即,朝廷在此设省,千年西域重新命名为新疆——新收复的疆土。
历史无法重复,但历史形态大概可以酷似。关于这段战火岁月,完全可能从史料中读出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味道,大势既已去,兵败如山倒,艰苦的战争,血性的战争,到了大势堪定的时候,也就如同捣碎垒卵一样从容了。解放战争是人民解放*的光荣,是对正义的诠释;左宗棠收复西藏的战争,则是晚清面子的挽回,也是千年西域本色的再现。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;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渡玉关。”据说这是左宗棠部下写的一首诗,其中的景象,在新疆美丽图画中,绝不能缺席。
禾木村美景胡广平摄三、不变的基因
西域、新疆,两个不同季节采摘的果子。它们的体质已实现了层级进化,在荒漠上独自求生的西域,依附母体欣欣向荣的新疆,脱胎换骨了,走向强壮了;但它们的体内却携带着一种代代传承的基因:*队、*事、*屯。这是留在它们身上的胎记,是辨识它们的标识,从其加入中原的那天起,就被注入到血液里了。因为遥远,就与*队发了干系,因为需要佑护,也只有*队才堪此任。公元前一百零五年,汉武帝在乌孙国首次实行*垦屯田。之后,除五代、两宋在西域的屯田暂且衰止外,其他各朝从未间歇。在清朝,西域屯田空前广泛,一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夕,*屯才遭到严重削弱。
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似乎不需要反复重申,锈迹斑斑的铁证都堆积如山了。
在新疆,在资料库里,我被屯田的故事打动着。我便认为,描写新疆,如果撇开*队,那一定是片言只语。
最令人触动的是当今的*屯。在两千多年里,没有哪个朝代能像今天这样大局磐定,所以也就没有哪个朝代像今天这样把屯田运筹得富有见识。建国之际,王震带兵屯于新疆,和历史上的屯田并无二致,一边生产,一边施诸武力,清匪除恶。随之,歹人灭,刀枪藏,*队迅疾转向国家建设,先农业,再工农业,再全面开花,最终把企业机制引入兵团管理。此间随时更番替号,不断赋予新的职能,把*人完全变成可随时出征的国民、突击队、抢险班,让*队的力量发挥到 。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创举!更令人感喟的是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宛如一台制造城市的机器,每个师都对应设市,至今十四个师的绝大部分都已设市,这是一种何其独特而壮观的屯*景象呢!
在新疆人看来,*队早已不是流动的战争机器,而是城外的一堵城墙,屋后的一道石冈,有了它,疆民们才吃得香,睡得稳。*队已浸润到每个角落,融进他们的血液里。他们无需着意于它的存在,也不会生硬地把它当作一个话题;然而,在他们所能感知到的世界里,桩桩件件都留下了兵团的痕迹。某某油田,某某农场,某某公路,都有一个主角,那就是兵团!哦,是的,公路,正是一条关于公路的故事,重重地撞击了我灵*,促使我不得不在这篇文章里讲一讲兵团。
独库公路,北起独山子,南至库车,穿天山而行,全长五百六十一公里。因为它的出现,所谓的南疆和北疆,就不再隔世般地孤立了。这样去讲述一条公路、实在显得平淡无奇,也许应该假设一个情景,如果让两千前的人制造卫星,登上月球,或是架设天桥飞度矮寨幽谷,哪怕他是唯我独尊的秦始皇,又有何计可施呢?独库公路建设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离现在算是很近了;但只有真正了解那里自然环境的人,才懂得修建这公路意味着什么。所以,当地人将这条公路视为神路。
一帮年轻的*人,历时十年,殒命一百六十八人;虽然这条路已变成二一七国道,但每年因为冰雪仍须交通管制七个月之久……时间就像一把钢刷,有关这条公路的惊世哀号,都被无情地刷去,只剩下一串数字。好在光芒毕竟穿透尘封,人们再次将这条公路和这条公路上的光点纳入视线。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寒冬,一千五百多名年轻的战士一夜之间被冰雪围困,结局只有一个:很快就会被冻死或饿死。某班长带领副班长及两名战士临危受命,背上仅有的二十多个馒头,去找指挥部、找组织!一路上,班长和副班长先后牺牲了,遵照命令吃下 一个馒头的陈俊贵和另外一个战友得救于当地牧民,一千五百条性命也保住了。延及到今天,故事的结局是, 一个馒头成为独库公路的光点,班长的事迹重见于世,陈俊贵因为守墓而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。的确感人!虽然听这段故事时,不免心生疑窦,难道悲壮从来就没有脱离人为因素吗?指挥部为什么没有主动解救战士?如此大的工程,保障措施在哪里?但是故事的确太感人了!修建独库公路的初衷,是摒除天险,结果却为“最可爱的人”拓展了内涵,成就了时代精神。
由那拉提去巴音布鲁克,我体验了这条公路,但那可能是最美、最无惊险的一段。沿着山体扶摇而上,似乎可以攀九天、入云霓,登一峰而小群山;特有的植被构成美妙的背景,再配以蓝天白云,独库公路的主色,就更加突出了。独库公路给我的印象是:惊艳!别致而惊艳!然而,这种体验却是摸象盲人之举。浏览大量影像资料才知道,独库公路何止是美的集大成者,更是凶险的代言者,因而也就成了挑战者的向往之境。如果还有机会,我将去用心地走一走。
九曲十八湾胡广平摄四、走过看过
迂回于新疆大地,总想说点什么。这种欲望,大概纯粹源自这里美丽、特异的风光。上帝在新疆创造了一个自然界的标本。上帝说:“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。”一切都以 的度量表现出来,繁茂到 ,荒芜到 ;广阔到 ,促狭到极至;冷到 ,热到极至……因而,这里便成了惯养彪悍个性的地方,成了自发吟唱的 处。“雪尽胡天牧马还,月明羌笛戍楼间”(高适《塞上听吹笛》句);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”(李白《关山月》句);“碛里征人三十万,一时回向月明看”(李益《从*北征》句)。太浩渺了,太遥远了,明月成为诗人们共同的慰藉。好在千里广袤之中,能怡人情志的不仅只有明月,还有处处的奇观。当代的旅游团社,只从中扣了一些点,供游人观赏,似乎难以“阅尽 春色”。其实这已经足够了,把点连接起来,由此及彼,带着游人们飞奔其间,宛如豪览自然奇观的大片,穷变极幻。也许很多人并不喜欢在这种位移中享受愉悦,而我却陶醉于此。日行千里的观光体验,使我捕捉到无穷多的信息,大脑里的存储盘太满足了。
从新疆返回后,存储盘似乎无法严密封存,时常迸发出一些火花,那是关于新疆之行的记忆。
从乌鲁木齐出发,走北线,跨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,宿北屯市,经阿勒泰,第二天到达一个名为禾木的宁静村落——其实是一个蒙古族乡*府所在地。一进村庄,便可以归纳出一堆将这里作为目的地的理由,清一色小木屋,宛若繁星撒落在山间坦地上,乍看上去杂乱无序,登高俯视却又街巷纵横;湍急清澈的新疆式河流横穿而过,河边便莫名其妙地出现白桦林和草甸,有人坐在圆石上陶醉,有马悠然觅食;村落被群山合围。山却没有半点险峻,全是所谓的高空草原,墨绿色松杉类常青树点缀其间,丛丛缕缕不绝。这时便觉得,禾木其实该叫集木,玩这集木的定然都是天人,堆砌出了怎样的绝妙呵!
不知旅行社顾忌成本,还是因自然所限,被他们当作 念叨的喀纳斯湖,实在未显其奇。从入口进去,仅看到一个巨大的出水口,水清流急,原生态杉树林与其为伴,本以为该吃一顿景观大餐了,却没有想到游览随即结束。好在沿出水口往下游走,处处都在补课,蓝宝石般的河凼,茂密的常青树林,依然牵走了放浪的神思。行进在新疆大地上就是这样,丝毫不用担心会被冷落。随之,在前往贾登峪的途中,视觉便获得了穷奢极侈,看不到边的山地草原,间杂以看不到边的杉树林,牛羊满坡,毡房如海。这应该就是北疆的主色调,也是牧民们的气场。
大概由贾登峪去布尔津,另一种画面缚获了整个视野。秋天淡*色的薄草,精细地裹着远山大川,看不到一处裸岩和杂物,没有树,也很少见牛羊和毡房,只有天和地在低语。加上朝阳的朗照,大地显得格外安宁、光洁和纯粹,而那种凭借柔美曲线的自我炫耀,让人实在无法不为之动容。然而,有经验的游侠却知道,荒漠正在逼近。果然,是荒漠将我们带入克拉马依,也是荒漠将这座石油之都渲染得格外与众不同。
夜幕初降,大漠似乎该到尽头了,便生动演示了一番剥极则复的卦义,博乐市到了。这正是一座因兵团而兴起的城市,有许多闪光点,阿拉山口口岸、全国卫生城市,无论哪一块牌子都会使之发亮。难怪一来到它的街灯下,我就觉得该重新定义僻壤的概念了。只可惜并没有在这里停留,夜入夜出,未曾记录下它的倩影,就投向了下一个目的地,有点像急行*。
行程安排明显偏爱了自然风光,但赛里木湖绝不会扫人之兴。大巴车沐浴着朝阳来到湖畔,天明显有些冷,便加了衣服。但我却顾不上捋顺衣襟,就忙了起来。每到一处,我都这样忙乱,忙着寻找 观察点,忙着把它们拍下来。我的价值观是,让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昂贵的付出中失之交臂,那一定在犯痴。赛里木湖畔的雪山、湖面上深蓝而怪异的天际线,让我一下想起纳木错湖。随之,感到新疆大地的贪婪和狡黠,盘踞着如此多的美景,还劫色于属于青藏高原的圣水,真让人对这里的美丽无以言状。
一晃六七天过去了,接下来便投奔新疆两个生命指标的极地:那拉提草原和巴音布鲁克草原。探访这么神异的去处,却随从一大帮人,似乎太不讲究了,但已然没有独自与其对话的可能。好在那拉提是宽容的,刚从川地出发,辽无边际的草地就以其纯洁温柔的怀抱慰藉着所有人。眼前的山坡和无限远的山坡,都绿得那么干净。很明显,这里的牛羊并没自由上山的特权,牧民们为冬季储存草料,在山坡草地上留下异常壮观的收割茬口。
作为大草原,那拉提盘踞着足够自诩的辽阔。作为旅游景点,游人只能止步于一块巨大阔地的中心点。这里因为人而热闹起来,也因为人而改变容颜。牲畜成了逗人开心的主角,剌鼻的粪便味,正好把影人们驱赶到稍干净的区域。我便看到眼前的雪山垂头不语,却依旧为这片生命福地输送着它们的血液。夕阳渐行渐西,巩乃斯河面反射出一道高贵的金光,食草的畜群显得更加优雅。它们的和谐,似乎在向造访者申明,洁净的河流、温热的阳光以及它们自己,才是这里的绝配。
离此不远的巴音布鲁克草原,似乎更加昭彰着自己的天性,绵延不绝的雪山把更多的辽阔让出来,使各种生物都显得十分丰美。天鹅留了下来,鹤类也随处显露身影。因水源丰沛,河流在这里折出一个九曲十八湾来;因营养过剩,草原竟多了一抹浅红色。巴音布鲁克,真是太别致了。
从大草原前往吐鲁番时,大地突然说:“你们好好活着,我将死去了。”大地便渐渐失去颜色,以至秃兀成肃杀的面孔,一时黝黑,俄而惨白。温度骤然升高了,逼着人在酷热中感知火焰山,或品味交河古城。我突然感悟到,不单这里的人活得很顽强,这里的大地也没有死,它们在以另一种形态活着。火焰山、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沙漠都一样,天生就是考验生命的考官。
交河古城胡广平摄五、西域絮语
新疆之行的整个过程都在收获异样的愉悦。尽管这样,准备结束行程时,仍有如释重负之感。能坐下来品尝葡萄和哈密瓜,使生活回到悠闲状态,应该是最完美的结局。但我内心感知到的不光是瓜果的甜蜜,甚至五味杂陈,我想到一些事,一些话,都是关于新疆的。
有时真不知道怎么了。一帮人在一起闲聊,只要关涉到宗教、民族,大家都讳如莫深、语焉不详了。是不能说,还是不好说呢?我们的西域,中国的新疆,多么无法辩驳的史实啊,决不会因为一帮人编造出一个什么“国”而改变!谁都应该尊重民族习惯,也应该尊重宗教;但被尊重的人同样要学会尊重别人、尊重良知。现在中国人都在讲“不忘初心”。在民族的教化上是不是也有一个初心呢?一定是有的,每种宗教的初衷,无不希望民族自身的兴旺、发达。“祸莫大于不知足,咎莫大于欲得”(老子语),作为民族的一员,不懂根本,只为一己所欲,把经往歪里念,真应该谢罪于自己的民族。
在新疆,的确无处不见栅栏、安检之类的管理措施,其中凝结了管理者无穷的心血。以殚思竭虑的辛劳,规范行为、体察隐忧,让人们得到一份心安,使生命受到尊重,这不好吗?况且无论外来人,还是本地人,无论汉族,还是少数民族,无论信仰伟大的共产主义,还是信仰某种宗教,都一视同仁,将严格管理变成普遍的社会行为,何侵犯人权之有?何民族歧视之有?
见不得人好,似乎是某些国、某些人恶的天性。我们的新疆好不好,由新疆的绝大数人说了算,由中国人说了算。少数人触底作恶,甘愿为敌,绝没有资格代表一个民族。至于某国家动辄针对别国在自己的国家立个什么法,何异于涕流垢面的孩童过家家?实在幼稚得可笑。面对其呱呱乱叫, 的做法是,在申明立场之后,予以漠视!
(本文作者胡广平申明:本文曾在